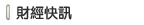投資要點
我們在1月2日《欲罷不能的寬鬆》系列報告之一——《後QE時代,歐央行何去何從》中,我們指出歐央行態度將轉變,考慮到TLTRO的到期節奏,最快可能在上半年延長TLTRO,這一判斷已落地。
本文為該系列報告的第二篇,核心在於分析美國企業部門的高槓桿問題使得美聯儲不得不退回至寬鬆。這一背景下,如果流動性預期修復的邏輯消化結束,當市場關注點回歸基本面,那麼可能意味著海外市場波動仍將上升。
•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十年寬鬆催生寬融資條件。
o 本輪美國經濟加槓桿的主體在企業部門,而非居民部門;
o 寬鬆環境催生融資條件寬鬆:1)“高評級”企業債中50%以上為BBB級;2)“低評級”企業債中槓桿貸款風險在快速上升。
•本輪美國企業加槓桿行至哪個階段?
o 企業槓桿率:與00年代初科網泡沫時水平相當;
o 高風險融資體量:槓桿貸款規模佔比與2006年次貸相當。
•企業債務的困境,美聯儲的慾罷不能。
o 過去央行通過壓低利率水平緩解高債務下的償付壓力;
o 但反過來看,這意味著利率水平被“綁架”;
•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短期或有波動,長期凸顯中國資產價值
o 短期:當全球流動性預期修復邏輯演繹結束後,美國金融市場脆弱性仍高,不排除會有波動向國內的傳染;
o 長期:美國資產也沒有那麼安全,反過來凸顯了中國資產的長期價值;
o 資產配置的建議:中國權益資產+黃金/波動率。
正 文
我們在2019年海外年報《山雨欲來》中指出,海外金融市場面臨大動盪。在2018年4季度全球金融市場已經歷過一輪大幅震盪,而自1月以來美股持續反彈,是否意味著海外金融市場的動盪已經結束?我們認為,從中期來看顯然並不是。當前海外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在於美國企業部門的高債務、高槓桿問題,當市場關注點從央行貨幣寬鬆轉向基本面後,這一問題將會再次暴露出來。
本輪美國經濟加槓桿主體:企業部門,而非居民部門
•本輪美國的主導部門:企業部門,而非居民部門。2018年下半年開始,市場開始逐步認識到,本輪始於2016年的全球經濟同步復甦可能已接近尾聲(我們最早於20181031《“驚喜不再”後,美國經濟會如何》中闡述這一觀點)。那麼,如何觀察本輪美國經濟能夠走多遠?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認為首先需要釐清的是,本輪美國經濟的主導因素是什麼?站在2013年初,我們看好本輪美國經濟復甦,並且指出本輪美國經濟是“不一樣的崛起,核心在企業部門”(參見20130422《不一樣的新周期——對全球再平衡的三重理解》 ,20121210《春後霧散看鷹飛》)。事實證明,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美國企業盈利、投資/GDP在金融危機之後的這幾年都相對於2000-2006年出現平台的上升。換言之,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的這一輪復甦中,企業部門是主導,這與上一輪週期(2000-2006年)截然不同的。
•……這也是為什麼本輪週期,美國經濟波動主要來自企業投資。如果從經濟的波動來源來看,可以發現2012年之後非農就業的波動與PMI的波動幾乎脫鉤,PMI波動遠大於非農就業的波動,這與90年代這一輪週期是相似的。而在2000-2008年那一輪週期中,居民部門就業情況的波動幾乎決定了經濟的波動。如果看GDP的支出法拆分,也會得出相似的結論(請參見20171011《本輪全球復甦的真相》)。
•因此,本輪美國經濟持續性的關鍵點在企業部門。從債務的角度來看,2012年之後美國居民部門是持續降槓桿的,其風險在於資產端受金融資產的波動較大(參見20181127《山雨欲來》)。而加槓桿的主體主要在企業和政府部門。如果我們暫時認為美國政府部門不會出現難以為繼的情況,那麼本輪美國經濟的延續性的核心關鍵點就在其企業部門。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十年寬鬆催生寬融資條件
•每一輪寬鬆週期都有著相似的路徑。如果考察歷史上的槓桿週期,會發現都有著相似的路徑:融資條件寬鬆/融資成本下降→債務增長→盈利下降/貨幣條件收緊導致債務難以為繼。而2012年之後的美國實際上也是沿著同樣的路徑,與00年代不同的是,加槓桿的主體由居民部門換成企業部門。
美國是典型的直接融資為主的市場,我們可以按照風險等級,從兩個方面考慮美國企業部門的槓桿情況。
•低風險(投資級)融資:沒那麼“低風險”。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鬆將利率水平壓至歷史低位。為了獲得足夠的收益,全球投資者不得不去尋找所有仍能夠提供高回報的資產(Hunt for Yield),這壓低了幾乎所有資產的收益率。反過來,這意味著企業的融資成本大幅下降,也刺激了企業的融資行為。
如果以投資級債券指數作為這一風險級別市場的表徵,那麼會發現投資級中的最低級別(BBB)的佔比已回升到上一輪週期的高點,即50%左右。當然,歐洲也面臨這一問題。
而這一問題在於,與企業融資相伴隨的是,提供資金的主體為投資級債券共同基金,這一類型的基金規模已是2008年底的3.5倍。而BBB級已是投資級中的最低級別,一旦整體需求環境惡化導致企業償付能力下滑,這些企業將面臨著調出投資級別的風險,那麼這些基金將被迫賣出這些投資級債券。這也是為什麼在2015年、2018年底這兩輪企業債市場波動中,投資級債券基金的贖回壓力也較高。
•高風險融資:從“高收益債”到“槓桿貸款”。從美國企業的低評級融資來看,在00年代主要為高收益債。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槓桿貸款變得越來越重要(何為“槓桿貸款”,請參見下面的專欄),甚至在近幾年高收益債的淨融資持續為負的情況下,槓桿貸款的淨融資仍在持續增長。當前貸款基金的規模已是2008年底的11.8倍。截至2018年2季度的數據,美國高收益債市場的存量為1.3萬億,而槓桿貸款存量已達到1萬億。
專欄:何為“槓桿貸款”?
•何為“槓桿貸款”?槓桿貸款(Leveraged Loan)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定義,其更像是對某一類企業融資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稱呼,其一般具備以下四個特徵:
o 銀團貸款:整個融資規模較大,通常超過2億美元,因此往往通過多個銀行共同提供;
o 投機級:融資的企業資質較低,或者企業負債率已較高,也對應著高利率,通常為Libor+200~300bp左右,最新的到期收益率為6%左右;
o 槓桿:企業做這筆融資往往用於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槓桿收購佔其資金用途80%-90%,這也是為什麼這類融資會被稱作“槓桿”貸款;
o CLO:槓桿貸款往往與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聯繫在一起,這是由於以槓桿貸款為基礎資產的證券化產品為CLO。60%的機構投資者槓桿貸款被證券化為CLO。因此兩者關係緊密。
•為什麼要看“槓桿貸款”?當前廣義的全球槓桿貸款市場約2.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槓桿貸款市場佔比在70%以上。狹義的槓桿貸款市場往往指被納入在“標普全球槓桿貸款指數”中的部分,約1.4萬億。
而截至2018年2季度的數據,美國高收益債市場的存量為1.3萬億,而槓桿貸款存量已達到1萬億。
•誰在買“槓桿貸款”?從投資者來看,非銀行機構投資者持有80%以上的全球槓桿貸款。而非銀行機構投資者中又以證券化產品CLO最為重要,約佔60%。CLO將槓桿貸款進行分層,銀行、保險、養老金持有其中風險等級較高的層級,而其他機構投資者如貸款基金、對沖基金等則持有其中風險較高的層級,以獲得更高的收益。
換言之,在槓桿貸款整體的投資者中,銀行、保險及養老金也有參與,但其主要投資於風險較低的層級,而基金會直接投資於槓桿貸款,也會通過CLO間接投資,其通過承擔更高風險獲得更高收益。
•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融資條件放鬆使得槓桿貸款風險在快速上升。在美國企業部門的低評級融資中,除了整體規模擴張以外,還表現為明顯的融資條件放鬆,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o 低門檻貸款(Covenant-Lite)佔比大幅上升。在傳統的槓桿貸款中,對企業的槓桿水平有持續的要求條款(Maintenance Covenants),即每次財報中的償付能力不得低於某一水平(如總債務/EBITDA不得超過5倍),否則將觸發一些懲罰措施,如增加融資費用、提高融資利率、補充抵押物等。而所謂的低門檻貸款(Covenant-Lite)是一種觸發式條款(Incurrence Covenants),即不要求每個季度的財報都滿足槓桿要求,而只有當公司採取某些大型行動(如收購)時才需要滿足償付能力的要求。很明顯,低門檻貸款對公司後續的行為約束是下降的。而在全球2018年發行的槓桿貸款中,低門檻貸款佔比已超過60%。
o 對融資主體盈利粉飾(add-backs)的默許低估了其槓桿水平。槓桿貸款融資時往往對企業的槓桿率有要求,然而在過去幾年的槓桿貸款中,對於企業槓桿率的計算要求出現明顯放鬆,允許企業使用預期潛在盈利(add-backs)計算槓桿率,這使得企業的實際槓桿率被嚴重低估。根據英國央行的測算,2018年全球槓桿貸款融資主體的槓桿率(總債務/EBITDA)為5倍左右,然而,如果扣除這種潛在盈利的計算方法,真實的槓桿率水平會上升至7倍以上。
事實上,融資條件的放鬆本質上來說反映的都是,過去一段時間融資主體和投資者之間的關係。在全球“資產荒”的大背景下,投資者不斷尋找高收益資產,使得在整個企業融資市場中,融資主體的溢價能力不斷上升,而導致整體的融資條件不斷放鬆。
本輪美國企業加槓桿行至哪個階段?
要判斷任何一輪繁榮的結束都是非常困難的,但至少我們可以和歷史做一個對比。
•企業槓桿率:與00年代初科網泡沫時水平相當。在過去寬鬆的貨幣環境中,投資者追求高收益,因此不斷降低融資主體的要求,反過來刺激了企業的融資行為。在槓桿貸款這種低評級融資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新發行的融資主體中債務乘數低於4倍的企業佔比已處於2001年以來的低點,而債務乘數在6倍以上的企業佔比也已超過30%,超過2007年。從整體企業的負債率來看,正如我們在2019年年報《山雨欲來》中所指出的,企業淨負債/EBITDA的中值也已回升到超過00年代初科網泡沫時的水平。
•高風險融資體量:當前的槓桿貸款VS 2006年的次貸,規模佔比相當,證券化低。正如前面我們所指出的,事實上歷史上任何一輪槓桿週期都是相似的。00年代時候,美國加槓桿的主體是居民,而當前是企業。槓桿貸款本身是一種資質較差的企業的融資,因此性質上與當時的次貸是相似的。對比兩者的異同,規模佔比接近,2006年美國次貸佔整體房貸市場的比例達到13%,而當前全球槓桿貸款佔發達經濟體企業融資比例為9%。條件更鬆的貸款種類占比也接近,2006年的次貸中有40%為“更次”的房貸,即沒有完整的文件,而當前60%的存量槓桿貸款為低門檻(Cov-Lite)貸款。從風險傳染的角度來看,當前杠桿貸款的資產證券化率明顯低於2006年時的次貸。
債務的困境,央行的慾罷不能
•為何美國企業高槓桿的事實會被市場忽略?——央行的作用。事實上,上述美國企業槓桿率上升的也是全球的問題。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債務存量/GDP上升了約60個百分點,對比上一輪週期(2001年~2007年)上升幅度為約20個百分點。所以,實際上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處於一輪持續加槓桿的過程中。(請參見《山雨欲來》)。
但有意思是,我們看到市場似乎並沒有“感受”到美國企業部門的高槓桿問題。另一個數據可以解釋這個問題——利息支出/EBITDA還處於歷史低位。換句話說,債務水平已高企,但由於企業所面臨的是持續的低利率環境,所以使得利息償付能力還未出現問題。
•反過來看,這意味著利率水平被“綁架”——央行寬鬆“欲罷不能”。換句話說,為什麼前兩年利率可以上升,但現在不行?過去兩年,無風險利率上升,但由於企業盈利推升全球風險偏好,全球“Hunt for Yield”,因此信用利差是壓縮的,企業尚未明顯感受到利息償付壓力上升。但當前企業盈利前景已經開始變化,這意味著信用利差可能將上升一個平台,而如果無風險利率進一步上升,則意味著企業償付壓力將快速大幅上升。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高債務意味著其償付能力對利率水平是更敏感的,而信用利差可能還將被迫上升,這意味著美聯儲只能重新壓低無風險利率。
對市場的啟示:需提防市場回歸基本面後的波動
•美聯儲結束縮表將部分緩解壓力,但企業部門的脆弱性並未實質性下降。美國企業槓桿率上升的這一問題,在經濟基本面較強的背景下,並不會對金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會提升ROE。但在經濟基本面逐步轉弱的背景下,將會成為明顯的負面因素。盈利下滑可能導致評級下調,進而信用利差擴張,融資成本上升,盈利進一步受影響,形成負面循環。
那麼,美聯儲即將結束縮表,導致流動性改善,這是否意味著風險下降?我們認為,信用風險可以拆分為流動性風險及違約風險,前者將隨著美聯儲態度變化而下降,但盈利環境決定著違約風險並未下降。一個簡單的例子是2014-2015年,全球流動性預期也發生了變化,美債收益率下降,但2014年3季度開始隨著美國基本面的下滑,美國資本市場波動明顯上升。除了美股以外,美國企業債市場,尤其是低評級的高收益債及槓桿貸款市場,仍有可能在未來1-2年面臨較大波動的風險。
•從時間節奏來看,全球金融市場已跨過流動性預期修復的初期,需關注當市場關注點重新回歸基本面後的波動風險。回顧2019年以來的全球股市,1月全球股市普漲,我們統計的70個市場中僅5個市場股市下跌。但2月全球股市已明顯分化,這顯示全球金融市場可能已跨過流動性預期修復的初期。而年初以來所公佈的海外經濟數據並不樂觀,尤其是日本、韓國的貿易數據顯示全球貿易需求回落較快。隨著流動性預期修復的結束,市場對基本面問題的再審視可能使得海外金融市場面臨波折。
• 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短期或有波動,長期凸顯中國資產價值。
o 短期來看,不排除會有波動向國內的傳染。
o 但長期來看,美國資產也沒有那麼安全,反過來凸顯了中國資產的長期價值,可能意味著整體資金流入的趨勢將進一步增強,有利於中國的權益資產。
o 資產配置的建議:中國權益資產+黃金/波動率。長期而言,我們依然看好中國權益資產的配置價值,但需對沖短期海外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可通過黃金或衍生品工具進行對沖。
風險提示:地緣政治風險超預期上升,市場波動率出現大幅變化。
本文作者:興業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王涵,來源:王涵看宏觀,華爾街見聞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