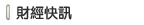本文作者劉剛、董靈燕,來自中金公司,原文標題《美股如果大幅調整,其他資產會如何表現?》
伴隨美股今年以來“一枝獨秀”的表現並不斷創出新高,投資者的擔憂卻有增無減,普遍擔心美股是否會在過度擁擠的交易以及過多獲利盤的“重壓”下因某些偶發因素觸發而大幅回撤,又或因為不斷上升的風險(如新興市場動盪、貿易摩擦升級)最終傳導回美股自身而導致其下跌。
上述擔憂不無道理,雖然我們認為美股短期風險並不來自盈利、估值偏高也並非泡沫,但依然面臨情緒上的擾動和資金面的約束;同時,如果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的話,美股市場也難以完全獨善其身(《貿易摩擦對美股盈利影響的情景分析》)。而考慮其在全球市場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股出現劇烈波動,勢必也會對其他資產和市場帶來一定影響。就此,本文中,我們針對美股歷史上歷次幅度超過10%回撤的情景,梳理了在美股大幅調整時其他資產的表現經驗,供投資者參考。
參照歷史經驗,如果美股大跌,其他資產和市場會如何表現?
雖然在基準情形下,從基本面確定性角度出發,我們目前對美股市場依然維持相對積極的看法和美>日>歐>新興這樣一個靠前的排序,但如果未來美股因為一些我們目前無法預見的突發意外事件和情緒上的擾動導致出現10%以上的大幅度回調的話,會對其他資產類別和全球其他主要市場產生什麼影響呢?
針對這一問題,我們整理了1929年以來美股標普500指數最大回撤幅度(MaximumDrawdown)超過10%的二十多次主要回調(圖表1);並在此基礎上,綜合考慮其他數據的可得性,重點以1976年以來的十幾次回調為樣本分析後發現,美股市場大幅回調期間,通常伴都隨著全球範圍內風險偏好的急劇惡化,表現為風險資產悉數大跌、而避險資產普遍上漲。具體來看,
首先,跨資產類別看,由於美股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和風險資產,因此其任何大幅度的動盪都會對全球風險偏好產生非常顯著的蔓延效果。對比美股歷次出現最大回撤的時間區間內其他市場和資產價格的表現(由於其他資產的波動區間不會與美股完全重合,因此這一計算方法未必能精確反映其他市場和資產的最大下跌幅度),平均來看,所有風險資產(主要股市、高收益債券、大宗商品、REITs、新興市場貨幣)無一例外都不能“倖免”、均大幅下跌;相比之下,避險資產如國債、黃金、日元則多數向好,這也凸顯了整體避險情緒的升溫(圖表1、圖表3)。
其次,分市場看,美股大幅回調期間,全球主要發達和新興市場悉數下跌,極少有市場能夠逆勢上漲;平均來看,回撤期間的表現排序為日本>美國>歐洲>新興(圖表3)。進一步細分市場,我們注意多數時間內,本幣計價下,約有一半的市場表現差於美股;平均而言,歐洲與部分亞洲新興市場明顯偏弱,日本和其他地區新興市場表現則要相對更好一些(圖表2)。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考慮到新興市場匯率在美股大幅回撤期間往往那個也會出現明顯的貶值,因此其在美元計價下的表現將會更差一些。
第三,從相關性角度,大跌期間美股與其他市場之間的相關悉數會顯著提升,平均是市場上漲階段的1.4倍;特別是部分新興市場,下跌期間與美股之間的相關性會提升至正常市場環境下的2倍以上(圖表4~5),這也說明美股大跌期間會因整體風險偏好降低而導致全球的共振。
第四,資金流向上,美股大幅回調期間,資金因避險情緒升溫會大幅流出股市、並相應流入債市。不過,資金流向在不同市場之間的輪動則並不顯著,這可能是由於資金流向本身存在一定的滯後性,因此往往會出現一些市場大幅回調期間,資金依然會持續流入一段時間的情形(圖表6~7)。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如果未來美股市場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全球風險資產特別是資金面開放的部分新興市場都可能會因為風險偏好的惡化而受到波及,因此此時單純在不同市場之間輪動可能無法起到很好的避險效果;相比之下,黃金、日元、國債等傳統的避險資產在對沖系統性風險的時候可能會更為有效。
不過,儘管如上文分析美股市場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甚至風險,但相比其他主要市場而言,其短期的增長確定性依然是最高的(圖表8),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從下半年展望《“險”中尋機,向確定性要收益》以來一直維持美>日>歐>新興排序的主要原因和依據。
基準情形下,我們當前對美股市場的整體看法依然是基本面向上(盈利預測趨勢而非增速)+估值向下(流動性收緊背景下難以繼續擴張)(圖表9)。我們認為,1)美股市場短期的風險並不來自基本面、儘管增速未來會逐漸回落(《美股2Q18業績:稅改與投資支撐強勁增長;增速或逐漸回落》)(圖表14~17)。2)估值高於均值但也並非完全的泡沫化(圖表18~20)。實際上,美股市場今年以來強勁表現的核心驅動力來自盈利,估值反而是收縮的(圖表10~13)。3)不過資金面是美股的一個主要約束,除了近期海外資金的回流外,基金在美股市場上的配置、美國居民部門的配置比例、以及美股融資賬戶隱含的槓桿水平均接近歷史高位(圖表21~24)。
圖表1: 1929年以來,美股標普500指數最大回撤幅度(MaximumDrawdown)超過10%以上的二十多次主要回調

圖表2: 多數時間,本幣計價下,約有一半市場的表現要差於美股;考慮到新興市場匯率通常還會出現的貶值,美元計價下表現可能更差
圖表3: 所有風險資產無一例外都不能“倖免”、均大幅下跌;相比之下,避險資產如國債、黃金、日元多數向好;平均來看,回撤期間的表現排序為日本>美國>歐洲>新興

圖表4: 對於部分新興市場,下跌期間與美股之間的相關性會提升至正常市場環境的2倍以上;這也說明美股大跌期間會因整體風險偏好降低而導致全球的共振
圖表5: 下跌期間美股與其他市場之間的相關性會顯著提升,平均是市場上漲階段的1.4倍
圖表6: 美股大幅回調期間,資金因避險而大幅流出、並相應流入債市

圖表7: 不過資金流向在不同市場時間的變化並不顯著,由於資金流向本身存在一定的滯後性

圖表8: 儘管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但相比其他主要市場而言,美股短期增長確定性依然是最高的
圖表9: 對於美股市場,我們當期的整體看法依然是基本面向上(盈利預測趨勢而非增速)+估值向下(偏高但並非泡沫,流動性收緊背景下難以繼續擴張)

圖表10: 換言之,今年以來美股屢創新高的市場表現核心驅動力來自盈利,估值反而是收縮的
圖表11: …絕大多數板塊都是如此

圖表12: 今年以來標普500指數7.4%的漲幅中,盈利上調貢獻17.3個百分點、估值反而拖累了8.4個百分點
圖表13: 即便是表現更為強勁的納斯達克指數,貢獻也全部來自盈利,估值基本持平
圖表14: 二季度標普500指數EPS同比增長23.1%,略低於一季度的24.2%
圖表15: 新訂單持續增加的同時,訂單積壓、交貨時間也也在加劇,表明整體呈現“供不應求”的狀態
圖表16: 得益於金融監管放鬆,我們注意到美國的工商信貸近期有進一步加速跡象

圖表17: 美股市場的盈利一致預測今年以來持續上調

圖表18: 從衡量估值水平的多個維度來看,儘管一些指標顯示的估值水平已經偏高,但綜合來看也並非完全的泡沫

圖表19: 當前標普500指數12個月動態估值水平為16.6倍,與長週期15.8倍的歷史均值基本相當,但明顯低於今年初18.5倍的高點
圖表20: 對比股市的動態收益率和相對實際利率的實際收益率來看,目前市場也不算很貴

圖表21: 配置在美股市場上的比例為56.4%,處於歷史相對高位
圖表22: 美國居民部門通過共同基金或者機制配置在股市上的財富比例也處於2000年科技泡沫以來高位,達33%
圖表23:美股融資賬戶隱含的槓桿水平已經接近3倍,為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最高位

圖表24:不過,最近一段時間不管是由於被動躲避新興市場風險還是主動追逐美國持續向好的基本面而流向美股市場的資金起到了一定的支撐效果